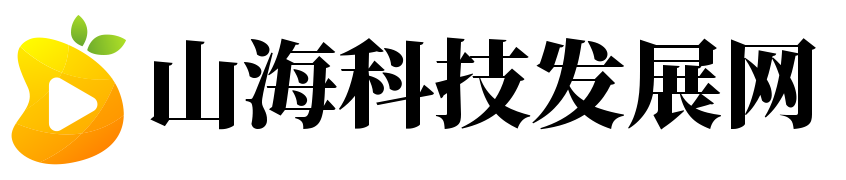拿着13000存款,我提前退休了

我们习惯了接受一种成功叙事。
无论是挤进越来越狭窄的上升通道,还是想象一种跳出圈套的生活,人们称前者为体面、稳定的“上岸”,后者是自由、享乐的的“旷野”,如今都成了模板化的想象符号,在这些主流的叙事面前,似乎从一开始,就隐去了普通人的话语权。“农村女性,学历不高,没有存款,家里不支持。”这是入阁在豆瓣“fire生活(穷版)小组”帖子里对于自身境况的回复。她在2023年3月带着一万三千元的存款逃出家,来到重庆,不上固定的班,不买新衣服,几乎不外出吃饭,剃了寸头,以很少的存款,和严格控制的支出平衡生活。事无巨细的账单里记录了她的日常。220元,是她在重庆一个月的房租,2元,是她在地铁吹空调、写生的交通费,3元,是今晚超市里折价的鱼,4元,是皮有点厚的西瓜。而这样看似极度压缩物质欲望、游离在社会价值体系之外的日子,却比大部分人更接近生活的原貌。入阁认真地对待一蔬一饭,给自己计划一顿不会太快变冷的年夜饭,观察植物的生长、鱼缸反射的光、路人的姿态,她的生活也因此变得明朗起来。
一个普通人,为什么想,又如何开始追寻自由?她放弃了什么,得到了什么?在入阁的经历里,有太多“不得不”的时刻,面对复杂而混沌的生活,她努力伸出手,抓住了一点想要的。
“2023年3月15日,妈妈抓回一只逃了几个月的鸭子,我担心是不好的预兆,因为17号是我出逃的日子。”
入阁在帖子里讲述她的出逃,这不是她第一次计划离开这个家。她出生在一个重男轻女的农村家庭,曾经几次“逃离”,又几次因为各种原因不得不回去。
第一次逃离发生在8年前,高考后,她报了1500公里外的大学读产品设计,目的是离家远一点。结果并不圆满,她在学校遭遇校园暴力,休学了一整年,复学后,她的状态没有恢复,只能去医院治疗,学校说这种情况需要家长陪读,或者让医院出具证明。入阁嫌“太麻烦”,主动退学了。
她回到家,做过半年奶茶店的工作,又做了几个月书局的工作,她先做仓管,后来做客服,都没能继续下去,入阁不想再上班了。
入阁觉得自己好像理解不了工作那套规则:“有时候我会在工作内容上比较较真,但他们会告诉我,你这个时候不需要这样认真。但有的时候,他们又说,你应该认真对待这个问题。”之前的遭遇也让她恐惧社交。上班两个字像日复一日的漩涡,让人被迫卷入,被动疲劳。
22年,入阁去了朋友在河北农村的一个“躺平基地”,因为疫情,那里只有她们两个人。她第一次接触这种“自给自足”的生活,“很享受地过了一段时间”。刚到那儿时是八月,大部分蔬菜已经进入采收期,每天都有吃不完的新鲜蔬菜,实在腐坏的就扔回地里埋了。日出而作,日落而息,偶尔补午觉,她们给南瓜花授粉,把多余的雄花炸着吃,入阁清理了一片朋友忘记采收的樱桃萝卜地,想开荒种白菜。村子里的夕阳慷慨了一整个秋天,有一次,她们和狗追着夕阳跑了二里地。
入阁和朋友常常看夕阳
直到冬天,朋友去北方旅行,留下她,她的猫,基地里的一条狗。收紧的防控让村里的情况变得不确定,有时买不到菜,有时出不了门。入阁陷入焦虑:“谁知道在这里还会遇到什么?”
去日本留学的念头也是那时候出现的,入阁在社交网站刷到了一个帮忙办理日本学签的团队,一时好奇进了群,根据对方的意思,入阁可以通过学签到日本,一边打工赚钱,一边上语言学校。像一根突然漂来的浮木,抓住它,就可以离开家,重启学业,也好像可以重启人生。
她想尽办法带着猫离开了基地,回家,隔离,缴费,办理护照,学网上的的语言课,等签证下来,入阁才发现和他们承诺的不一样。
“原本说好是一年的学签,结果变成六个月,我觉得没保障,就去问了,他们很心虚,我一提就说要给我退款。”入阁很崩溃,“本来我什么都准备好了,甚至猫咪也打算让家里人照顾,最后还是和中介掰了。”
去日本的希望破灭后,入阁的心情跌落到了谷底。“我很害怕自己是一个无能的人,做不到任何事。妈妈说,要帮我找个工作,让我好好安稳下来......我一听就头皮发麻。”
入阁的爷爷奶奶是农民,父母都是工薪阶层,在家里,类似要她“安稳点”的话,她听过很多次,还有偶尔被说出来的后半句:“不工作,就嫁人吧,但你没工作,也没有男人看得上你。”入阁想逃,再也不要回去,她不想重复上一辈的生活。
一开始,她并没有一个详尽的计划。她打算去包头投靠朋友一段时间,再看下一步怎么办。她带上了之前兑换的15万日币(折合人民币7000元左右),和一张之前工作存下来的、有6000元余额的卡,因为害怕被家人拦住,春、夏、秋、冬的衣服,她只各带了一套。
2023年3月17日,入阁和妈妈说“打算去散散心”,离开了家里,跳上去往包头的列车。
被妈妈捉回来的鸭子
一间自己的房间
三月的包头很冷,到处都在结冰,入阁出门写生,再回朋友家,外面是冬天,家里又是夏天,她把唯一的外套脱掉,换上唯一的夏装。
包头只是她的中转站,前几天,奶奶发消息说猫丢了,虽然后来又找到了,她还是很愧疚,不想呆在离家太远的城市了。
“我一开始考虑的是去云南,但云南的租金有点贵。那种自建房隔断出来的一居室都要五、六百一个月,价格再低的话,条件更差了。”她仔细看了看从包头到云南的火车,发现中途会经过重庆,又切回租房软件,搜索重庆的房子,“然后,我就找到了一个完美符合我预期的房间。”
入阁口中的“完美符合预期的房间”,月租220元,在城中村,14平米,没有怎么装修,只是简单粉刷,但麻雀虽小,房间自带厨卫,有一张床,一个书桌。筒子楼里的老房子,窗户带着铁杆,小学、初中时她去县城里读书,家里帮她租的就是这一种,入阁猜想这类房间会有蟑螂,但她不介意。
她立刻决定了,她一定要租下这个房子,在重庆生活。
租房软件上的样子
初到重庆的那个下午,入阁觉得一切都是新的。她坐公交去约好的地点看房,高铁是始发站,只要坐三站,她提着一个重重的包,等车,上车,到站,下车。她兴奋地回忆:“当时很开心,真的很开心,我甚至觉得那些乘客也是开心的。”
下车之后就是一个大平台,老年人在纳凉,一些人在卖菜,人来人往。往下是一溜的店铺,再往里走,是城中村典型的平房,老房子旁边有地方正在拆迁,入阁有些担心:“不会我住了几个月就要搬走吧?”然后她见到了房东,也看到了那个房间,“我觉得和我小时候住的那个房间很像”,入阁这样向我描述它,尽管厨房里充满了油垢,没有空调,没有热水器,没有油烟机,也没有风扇......对于她第一个独居的、完全属于自己的房间,她很满意。
入阁很快签了租房合同,一次性付了押金和三个月的房租,拿到钥匙,关上门,打开电脑,开始玩游戏。其实她并不沉迷于游戏,后来的日子也很快不再玩了,但那个晚上,她玩了一整个通宵。玩一会儿,收拾一会儿东西,挪一会儿床,挪一会儿书桌,她知道楼下住着人,害怕吵到对方,就以一种很慢很慢的速度拖动这些家具,直到把它们搬到想要的位置。
打理后的小家
城中村养着鸡,凌晨三、四点的时候,鸡叫了。屋子旁边是一个有着彩钢板屋顶的平房,猫在上面打架,声音很响,隔壁楼的天台有只狗,听到动静后跟着大叫。入阁隔着窗户,兴致勃勃地看它们怎么吵架和打架,等天彻底亮了,她终于躺到床上,因为没有被子,盖着冬天的衣服睡着了。
独居生活的一切,都让人亢奋。第二天,入阁列了一个详细的表,给这个房间慢慢添置必需品,很快,这里被拾掇成了一个“小家”。
她喜欢在附近散步,有五金店,菜市场......甚至燃气站,一切都是触手可及的、便利的。她做了好几罐泡菜,萝卜泡菜、韩式泡菜,还有重庆人爱吃的川渝泡菜。她在燃气和电磁炉之间算了笔账,最终花了50多元买下电磁炉,她惊讶地发现,在不用迁就别人口味之后,原来自己是挑食的,比如,她不喜欢吃芹菜,相反的是,她突然爱上了香菜。她买了面包机,认真做了几次吐司,吃了几次三明治,后来拿它专职揉面,做馒头和油泼面。她有了一株小仙人掌,一个鱼缸,摆在窗台上,重庆总是阴天,但偶尔也会透进阳光。
重庆的鱼常打折,这顿不到4元
早上起来,被鱼缸的光美到了
重庆14㎡的生活
夏天要到了,整座城市变得燥热,食物的腐烂变得迅速。当入阁见证一块煮好的肉,在两个小时内“长满苍蝇的后代”时,她决定买一个小冰箱。房东阿姨拿来了风扇,阿姨的女儿和她差不多大,总是特别关照她。
经历了一开始的兴奋后,入阁建立起朴素的日常,因为激动而做的那些泡菜,最后只吃光了一罐,让她有些懊恼。她逐渐学习怎么控制买菜的量,摸索自己的进食习惯,为了减少开销,她没有点过一顿外卖,几乎餐餐都是自己做饭,真的不想做了,就去买韭菜盒子或者烧饼,都是2元一个。有一段时间,她会把它们写下来,明天要吃什么,冰箱里还剩什么。
她在豆瓣小组的帖子里写自己做的饭,以及省钱的攻略:
“超喜欢会放折价鱼的超市!刚死的鱼,剖干净了放在折价区,拿回家当天吃基本没差~”“划重点!不爱吃的菜不要强迫自己买来吃,冰箱小一定不要买太多菜,浪费是一回事,菜发霉了收拾起来也麻烦,尽量一顿吃多少、做多少,两顿吃不完就要扔了,节约归节约,吃出毛病了更不好!”“重庆公交卡9折,1小时内换乘直接免费,于是我夏天经常去轻轨里吹空调。”“没有买新衣服(朋友送了我两身过冬的),在二手群付邮+一件几块钱,买了一件毛衣、一件牛仔裤和一件套头卫衣。”
入阁的吃饭日记
日本作家吉田忍在著作《东京8平米》里,这样描写她8平米租房的生活:“也许8平米在别人眼里是畸形状态,但它能够让你活在自己的世界里......在那里你不用伪装,可以好好地面对自我,尽可能地去享受当下。”
像书里说的那样,入阁小心地经营着她14平米之内的世界,也因为家的“小”,转身走向外面的世界,保持和社会的连接。有时候,她会打开地图,搜寻家附近的免费景点,一个寺庙,一个公园......她还喜欢坐轻轨。
“我会先坐3、4站公交到轻轨站,根据重庆公交卡的规则,刷过公交后一小时内进入轻轨是免费的,当时在轻轨里的时限有270分钟,我常常待在里面,一条线从头坐到尾,又坐回去,一边乘凉,一边画乘客。有几条线可以看到江边,那些景点我从来没去过,但我在轻轨里见过洪崖洞和嘉陵江。”
学产品设计的入阁喜欢画画,为了锻炼自己的能力和精力,她在轻轨里写生,随机画遇到的乘客,只要对方没有动,她就马上画下来。完成一幅小画只需要1-2分钟,一趟地铁下来,最多的时候,能画30-40个人。她翻本子的时候发现,有三分之二的人都在玩手机。
玩手机的人
“太久没有画画了,一开始我画得好烂,但我还是鼓起勇气,我要成长,不要做焦虑的人。”入阁给自己打气。轻轨里看她画画的小孩子最多,总喜欢围着她。有一次,她画了一对带着婴儿的夫妻,小朋友的妈妈拍了照。入阁想把画撕下来送给她,但又想,自己明明画得不够好,这么做有点不好意思。
有一天,入阁发现居民楼门口的平台上,有嬢嬢剪头发,只要五块钱。她拿着之前寸头的照片过去说:“帮我剃成这样吧!”嬢嬢反问她:“真的吗?你不会后悔吗?你会难受吗?”
就这样拉扯了五分钟,对方才终于同意了。其实之前入阁就尝试过剃头,身边的人总以为她失恋了、发生大变故了,但她只是觉得这么做能凉快一些,洗头也不需要那么多的洗发膏。她想变得自信一些,挺着肩膀走路。
“我就是想让自己舒服,不想在意别人怎么看。”
“剪发嬢嬢的女儿是聋哑人,后来每次我路过,她们都会和我打招呼”
折返与重启
“我中间回家过一次。”入阁坦诚地告诉我,这并不是一个坚定逃离的故事。“2023年5月28日那天,奶奶突然发消息说,我的猫快不行了。”
入阁的猫叫张豆豆,一只可爱、有个性的三花猫,额头上有棕色和橘色的斑点。入阁马上买票回了家,因为生病,豆豆精神不好,毛发变得杂乱、肮脏,见到她以后,“一直叫,好像是气我抛下它走了。”
入阁发现豆豆的身上长了一个脓包,农村没有条件,县城的宠物医院拒绝治疗,她自己买了针筒、酒精、消毒喷雾,把伤口剪开清理,豆豆也很争气,伤口很快结痂了。入阁突然想,自己没能去日本是对的,要是一切顺利的话,就救不了豆豆、再也见不到豆豆了。
给豆豆做完手术后
入阁动摇了,自己是不是也能一半时间在家里,一半时间在重庆?她想着可以做一些手工,这样两边都能摆摊卖钱。但就在她准备开始的时候,意外发生了。
村子里自建房的工人因为操作失误,让运输材料的斗车砸伤了入阁的膝盖,她去医院缝针,却被奶奶指责“不该在那个时候出门,早点出门就不会受伤了”,入阁想要让肇事者承担医药费,家里没人支持她,妈妈说肇事者“是一个老光棍”,让她“不要太欺负人家了”。
“为什么不是我的错,但所有人都要我承担?”入阁自己报了警,找了村支书,最后只要到了500元检查费。她拖着还没恢复好的腿,联系了托运公司,打算带着猫一起走。“我彻底呆不下去了,之前想要两边跑的想法完全被打消了。”
她拉黑了亲人的联系方式,再一次回到重庆,入阁的身边多了豆豆,又好像只剩下豆豆。卡里的余额只有3000多了,她不得不去找兼职,一份小孩作业托管的工作,每天工作三小时,下午5:30开始,试岗时一天70块,定下来之后是一天80。入阁每天坐1个小时的公交过去,她往往会提前一点,不想让对方觉得自己是不守时的人。去上班时,她常常遇到之前的剃头嬢嬢,嬢嬢的女儿是聋哑人,热情地向她打招呼。
工作的地方有一家永辉超市,八、九点下班,正好会遇上折价菜,入阁会挑一些带走,蔬菜一、两元就有一大把,肉类也只要八、九元一斤。
寒假开始前,老师问入阁愿不愿意带寒假班,假期里带10天,就有1300元。入阁想存点钱好好过个年,就咬咬牙同意了,备课、上课、备课、上课,有时候她觉得自己讲得颠三倒四,回到家会痛批自己“怎么这么不专业!”第二天又重振旗鼓,她很担心“我是什么都做不好、特别差劲的人。”
入阁觉得“孩子们会不会瞧不起连备课都备不好的她”,却在很久以后的分别时,收到了她们的零食、小礼物、一个热乎乎的汉堡。托管班的孩子得知她要离开很伤心,她们问:“你会不会记得我的声音和长相?”“你会不会只记住这是一个学生?”“你会记住我多久?”入阁给她们买了本子,她们一定要她在上面写上名字、画上自画像。
寒假班结束时,除夕也快到了。老房子的过年气氛很浓厚,房东在她常去写生的寺庙里领了对联,贴在走廊里。入阁给这个年留了五百元预算,包括年货零食、年前两周以及年夜饭的食材,她记录自己的支出:
“买了猪板油和一桶大豆油,另外就是面条和饼子,真的好爱饼子。”
“小年那天去买了鸡蛋和肉,鸡翅中降价了必须买。”
“年二十八去很远的超市买了宝肋肉,打折人员给了我便宜的价,切了一片做小酥肉。”
为了这顿年夜饭,入阁规划了好几天:什么时候开始做,几分钟切菜,给肉焯水的同时要做什么,下一个菜什么时候开始......房间里没有空调和取暖,冬天的菜凉得很快,她得保证这顿年夜饭在吃的时候,大部分还是热的。
年夜饭的详细步骤,入阁写了一份word文档
“最后还是挺成功的。”除夕那天,入阁给自己做了八个菜,有鸡有虾,有荤有素。第一次做乾隆白菜,意外很好吃,而为了给过年一个“吃饺子”的仪式感,她特意做了蛋饺。
看着一桌子的年夜饭,入阁想起了两年前。“当时我在西安,因为有合租室友,不算完全的独居,我也做了年夜饭,和家里人视频通话,他们还夸奖我的饭菜。但今年不一样了,我把他们都拉黑了。”
“我讨厌我的家庭,但又渴望一个完整的家。我每次都会告诉自己不要再想这些不属于自己的东西了,但还是忍不住幻想,是不是也能和平共处,是不是也可以互相发发消息......”
入阁一个人的年夜饭
入阁刚离开家到重庆时,坐了很久的公交去找朋友,路上,她接到妈妈的电话,妈妈问她是不是再也不打算回来了,入阁回答“是的”,妈妈说:“你要当只流浪猫吗?”入阁说:“是,我是只流浪猫。”
入阁到重庆满一年时,在豆瓣分享了这一年来的所有花销,支出22632,收入23790,她计划在存够13000(和刚到重庆的数目一样)时,换一个城市生活,像电影《百万元与苦虫女》一样。
她希望自己做手工摆摊的想法能够重启,不浪费自己买的那些材料,之前她做了50个钩针,因为托管班的工作搁置了。
在帖子下,她收到了很多羡慕和佩服,入阁朴素地回复着:“世界那么大,人口七十亿,我们总会有不同的路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