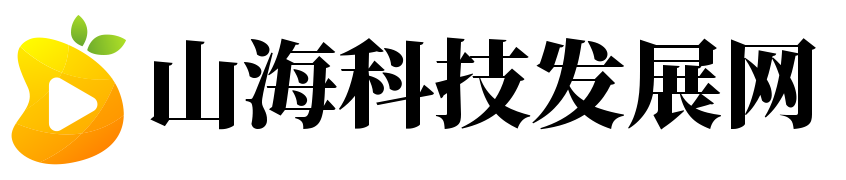诉讼离婚困局

感情破裂与否
两次起诉离婚后,阿曼对代理律师唐一菲说,她不想再走法律程序了。从2022年到2024年,她花了近两年时间打离婚官司,最终还是没有得到法院的支持。诉讼离婚困局!
阿曼的离婚案在立案时就遇到困难。阿曼生活在湖南,她的丈夫在外省的监狱服刑,第一次起诉离婚时,唐一菲选择在阿曼住所地(户籍所在地)的人民法院。2022年10月立案后,经过反复沟通才实现线上庭审。第二次阿曼选择在经常居住地(当前常住地)离婚,法官劝阿曼撤诉,“我不可能去外省开庭。”唐一菲据理力争,“在原告所在地起诉是符合法律规定的,为什么要撤?”随后唐一菲再次与被告服刑的监狱沟通,通过监狱内的科技法庭线上进行,庭审才顺利推进。
直至2022年,阿曼的婚姻持续了20年,男方有8年时间都在服刑。他们经由朋友介绍认识,2002年结婚,2009年生育一子,2012年男方因经济犯罪被判12年,此后两人保持书信交流。在男方的狱中来信里,他对自己过去吸毒、出轨的事情表示悔恨,对阿曼帮助其戒毒表示感谢,而阿曼在信中鼓励男方安心服刑。
第一次审判的法官根据这些信件判断,阿曼与男方的感情“并未彻底破裂”,在2023年3月21日作出的判决中,法官驳回了阿曼的离婚请求。
半年后,阿曼在长沙市的区级人民法院提起第二次诉讼,她的要求没有变,离婚并争取儿子的抚养权,她的儿子还给法官写了一封希望父母离婚的信。男方这一次没有反对离婚,但要女方等他出狱再离,并想争夺其入狱七年后女方购买的房屋。判决在2024年3月18日作出,法官认为阿曼与男方结婚多年,育有一子,有感情基础,男方不同意离婚的意愿强烈,所以不准予离婚。
唐一菲对判决结果感到意外。作为专门代理婚姻家事案件的律师,过去几年里她每年接触上百个离婚纠纷,经验丰富。第一次判决结果出来时,唐一菲像安慰所有当事人一样告诉阿曼,“首诉不判离”是一个默认的规则。近几年她代理的离婚案中,只要对方不同意离婚,就很难第一次在诉讼中获准离婚。有时候法官也会无奈地跟她说,“唐律师,你知道最后的结果是什么。”
第二次起诉很大可能会判离,坚持起诉在一定程度上显示了当事人离婚的决心。然而在阿曼的案例中,在双方分居多年且被告因服刑长期缺席家庭生活、无法承担家庭责任的情况下,唐一菲不明白为什么第二次也没能成功。
“感情是否破裂”一直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婚姻法》(以下简称“婚姻法”)衡量婚姻关系能否持续的标准。1980年修订的《婚姻法》进一步将这一标准作为判决离婚的法定标准。在司法实践中,如何认定感情破裂?1989年最高人民法院曾列举出14条认定夫妻感情确已破裂的具体意见。2001年修订的《婚姻法》中将法定情形减少至5种,“一方被依法判处长期徒刑”、“因生理缺陷或其他原因不能发生性行为”等被删除。2021年开始实施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延续了5种法定情形的规定。
唐一菲看过所有当事人的结婚证,除了一个为骗拆迁款而结婚的人以外,每一个人都是开心的,没有人会想到最后的一地鸡毛。在唐一菲的主观判断里,大多数提出离婚诉讼的当事人对目前的婚姻已经死心,“所有客户来的时候,我都会问,小朋友考虑清楚了没?你到底决不决定离这个婚?之后的想法可以改变,但此时此刻他们就是下了离婚这个决定。”不同意离婚的一方也未必存留感情,更多的是抱有执念,“有的人哪怕是过错方,也不会甘心放手。”
但在判决中,只要没被认定为“感情确已破裂”,唐一菲和委托人就需要再等上一年,收集分居证据,再次提起诉讼。除了5种情形以外,法律还有一条规定——“经人民法院判决不准离婚后,双方又分居满一年,一方再次提起离婚诉讼的,应当准予离婚。”唐一菲的大多数委托人都是通过这条规定来实现离婚的,“比起证明感情确已破裂,证明分居容易得多。”
漫长的等待
“一定要分居吗?”包惠问唐一菲,她前不久拿到第一次起诉离婚的判决书,正在为第二次起诉做准备。她是个生意人,在长沙市区有门面要照看,尽管早已搬进自己独居的房子,但她觉得收集证据很难,“每天早出晚归,跟周围的邻居碰不着面。”唐一菲教她:“在门口安装监控摄像头,定期保存内容。”
“可是我就见不到我儿子了。”包惠说出真正的担忧。她的儿子是中学生,跟丈夫一起生活,她无意争夺儿子的抚养权,但希望能时常见到儿子。“我儿子晚上回家,我都会给他倒杯水……我儿子很讲究,他的白衬衫领子要用手洗,菜做得不精致他都不吃。”
唐一菲耐心地劝她不要在家里见面,第一次诉讼开庭的时候,男方以她回家照顾儿子为理由,反驳了分居的说法。为了在第二次诉讼开庭前收集分居长达一年的证据,包惠不得不克制自己对儿子的母爱,这让她感到十分焦虑,“如果能早点判,我少分一点钱都愿意,早点判我能轻松一点,过好我自己的生活。”
包惠作出离婚的决定不容易,她年过40岁,认为离婚是一件羞耻的事情,去法院离婚的名声更不好听。她的母亲也不支持她离婚,“只有男的不要女的,没有女的不要男的。”2022年丈夫在吵架时提了三次离婚,包惠的态度从不想离婚逐渐转变为坚决要离。在她第一次去律所咨询那天,丈夫追着她吵架,她躲进派出所,随后丈夫及其亲戚来派出所大声叫喊,要让她净身出户。
“没有尊严。”被问到为什么要离婚时,包惠回答。“二十多年了,他们家都是这样,根本不懂得尊重人,认为女人嫁到男人家就是给男人做事。”包惠跟丈夫白手起家,从农村来到城市做生意,渐渐积攒起家业,她每天都在忙店里的事,同时还要承受丈夫的管束和猜疑。
丈夫不许包惠跟异性一起吃饭,如果发现她有往来的异性朋友,甚至会去找对方的麻烦。包惠给业务员送礼表示答谢,也被怀疑是出轨。实际上包惠对待感情很理性,“如果想在生意上跟对方长期合作,就不能有不正当关系,我怕别人以后拿捏我。”而丈夫则与店员有过暧昧关系,被包惠发现后,写过不再往来的保证书。
除去多疑,包惠最不能忍受的是丈夫性格中的暴戾。有一次她在晚上闭店后去直播工作间学习线上卖货,回到家被丈夫一顿盘问,争执之下丈夫用力地掐住包惠的脖子,“我从那个时候起就想离开,他掐我的时候,眼白部分是红色的,像狼一样。”
以往的很多细节让包惠相信自己身处险境,“我们认识几个月我就不想跟他谈(恋爱)了,他说要去烧我家的房子,我那时候20岁,没见过世面,又想快点嫁出去,独立挣钱,还是跟他结婚了。他一直很冲动,我们出去进货的路上吵架,他突然把方向盘打到底。当着小孩子的面吵架时,他拿着汽油威胁说要一起死。”
包惠急于摆脱婚姻关系,“(离婚后)我想干什么都行了,哪怕挣得少一点,我有自己的生活,能正常地结交朋友。”但她认为自己的想法没有很好地在庭审上表达出来,“开庭前跟法官没有任何沟通,庭审上问的是基本问题,什么时候结婚,有几个小孩,为什么想离婚。我内心的理由就是想躲开。我说他有家庭暴力,没有责任感,很恐怖。庭审后法官问能不能调解,就结束了。”
原本包惠的离婚诉讼采取简易程序,审限为3个月,因法官生病,她的案件转入普通程序,审限变为6个月。而民事纠纷在立案之前还需要经历诉前调解,法院的调解员会询问婚姻当事双方是否有和好的可能,等待调解同样需要付出时间。根据唐一菲的经验,地级市县的法院大概要等一个月左右,长沙市的区级法院则至少是一个月以上,人口集中的岳麓区有时要等待近半年。自提交诉状后,包惠经历了大半年时间,才得到了一场半小时内结束的庭审,以及第二次离婚诉讼的“入场券”。
等待庭审期间,包惠多次与丈夫沟通,希望能够协议离婚。相对应的,唐一菲也写了数版离婚协议,她发现与包惠丈夫的沟通是徒劳的,“今天同意签字,让准备好离婚协议,明天去民政局就假装忘带户口本。”但下一次“同意签字”,包惠还是会去准备——万一是真的呢?协议离婚像是戏耍包惠的一个虚无的奖励,漫长的诉讼程序加深了这场“游戏”累积的痛苦。
唐一菲在律所的儿童看护房看案卷(郭立亮/图)
拖延作为一种方法
由于诉前调解和“首诉不判离”的默认程序,唐一菲的当事人需要花费至少一年半的时间才能通过诉讼程序达到离婚的目的,她有些不理解,“与其一直拖时间,开几次庭,不如认认真真开庭,把事情讲清楚,这样不是更节省司法资源,也不浪费当事人的情绪吗?”
拖延带来了一些客观的变化。近20年来,我国离婚率经历了先增长后下降的趋势。据《民政事业发展统计公报》,2004年我国离婚率为1.28‰,此后持续增长至2019年的3.4‰,当年办理离婚手续的有470.1万对。2020年离婚率有所回落,为3.1‰。2021年“离婚冷静期”实施后,连续两年离婚率降至2.0‰。
每年全国法院一审结案的离婚纠纷在总体上也保持着上升的趋势,2016年以后,数量保持在140万件左右,2023年达到170余万件。同期的民事案件审理数量上升更快,2014年民事一审结案数量为80余万件,2023年变为了170余万件,9年间案件数量增长了一倍多。
与此同时,法官人数却在减少,2017年法官员额制改革后,全国法院的法官人数从20万左右降至12万左右。2023年最高人民法院审判管理办公室主任廖向阳在直播访谈中介绍,“2022年基层法院的员额法官人均结案274件,其中有9个省(区、市)的基层法院人均结案量超过300件,最高的超过400件。”
香港大学法律系教授贺欣研究中国离婚法条的司法实践,访谈了多名有丰富家事案件审判经验的法官,有的法官告诉他,“我一进办公室,第一件事就是打开电脑,查看当天等着我的案件……有时候光是看电脑上的案件清单就头疼。”由于庞大的案件数量和审理期限,基层法官承受的压力很大,而在一个离婚案件的审判中,判决离婚要花费的时间是判不离婚的5到10倍。
贺欣在其《离婚在中国》一书中记录了一名30岁出头的宋姓法官的观点,“对于大多数第一次提出的离婚请求,不管感情关系是否真的破裂,我们都不会批准离婚,除非当事人自己已经把一切都解决好了。为什么?如果我同意离婚,我有责任分割他们的婚内财产和子女抚养权。财产分割是一个极其棘手的问题,有时候,从一套房产到一个茶壶,你都要分……不管我们怎么分,投入多少时间,双方都可能不满意。”
唐一菲也见识过财产分割过程中人性的自私,围绕财产的争端层出不穷。曾有被判决离婚的一方心怀不满,把没有分给他的房产内装砸坏,理由是判决书仅仅写了房产,而没有把装修算在其中。之后唐一菲再写诉状时,会把装修、家电等细节都加在房产之内。
法官判决离婚就会陷入到这些麻烦纠纷中。贺欣认为,出于效率的考量,法官在第一次起诉中会倾向于判不离,“事实上,对于任何争议很大的案件,即使当事人不是首次提出离婚,拖延裁决也是法院普遍会采取的一种策略。”这样做的风险很小,因为“感情破裂”有很大的解释空间,即使不满意的当事人提出上诉,二审法院也很少推翻不准予离婚的判决。
这样的“拖延做法”一定程度上给了双方当事人缓冲的余地,让双方有更多时间来接受最终的结果。贺欣观察到,有些法官担心匆忙判决离婚会导致不良的后果,“男人的情感和心理状态可能会导致他对通过离婚寻求独立的妻子实施暴力。”
在陕西一件原告为女医生的离婚案中,贺欣旁听了庭审和调解过程。原告下定决心要离婚,说不离婚就“去死”,被告的态度同样坚决,他对法官说,如果判决离婚,他和原告会一起死。经过几轮调解,被告仍然对法官说,“如果这件民事案以离婚告终,你们就会在刑事法庭上见到我。”
一位法官对贺欣说,“未经慎重考虑的离婚判决可能会将冲突转移到法院,这对法官来说太过分了。”另一位法官说,“一些法官受到诉讼当事人的骚扰、威胁和羞辱,这在一定程度上迫使法官在处理离婚案件时极为谨慎。”
在陕西的一场庭审中,妻子控诉遭到了婆婆的家庭暴力,并且因丈夫性无能而无法过正常的性生活。法官对妻子的律师说,即使这段婚姻无法持续,但这一次也不能离婚,因为要“尊重丈夫最后的尊严”,“我们必须保持这段婚姻的形式。让我们给丈夫的家庭一点时间,让他们从心理上做好失去她的准备。”
但对于已经遭受家庭暴力威胁或伤害的一方而言,有时候拖延本身就是一种伤害。
二次准备
陈若莲第一次见到唐一菲是在一次严重的家暴之后,她从生活的H县逃往长沙,带着一身淤青和一双被硬生生掰掉甲床的手。在唐一菲的陪同下,她第一次去做了伤情鉴定。
陈若莲经历过无数次家暴,从她18岁谈恋爱起,男方就有过暴力的行为,当时她觉得这是“小事”,不想因此断掉感情。结婚后,暴力行为一次次升级,“一般我被打到趴在地上,他还说我是装死,又抓着我的头发把我提起来。”陈若莲今年43岁,对男方早已没有爱,对这桩婚姻只有悔恨和恐惧。
因为恐惧,陈若莲对很多事情做出了让步。她容忍男方出轨,男方直接在钱包里放其他女性的照片,和其他女性公然交往。她承担着全部的家庭经济压力,每个月要给男方3000元生活费,孩子的教育和零用也由她来支付;她在县城买了一套房,又在长沙市贷款买了一套房,还背负着七八十万元房贷。在庭审中,男方承认了陈若莲对家庭的经济贡献,对法官说,“钱都是她赚来的。”
“出轨可以,依靠我生活也可以,但我真的不能再忍受家暴了。我提醒过他很多次,再动手打我,肯定不会跟他过了。他无所谓,说什么也不听。”陈若莲从来没有过实质性的反抗,她被打得最厉害的一次,脖子被掐得淤紫,男方甚至拿起了刀,她十几岁的女儿报了警,警方把刀夺走后,她还是选择了不处理。
指甲被掰断的那次家暴之后,陈若莲才真正下定了决心,她想带着女儿离开。女儿同样遭受着男方的暴力对待,“她读幼儿园时,算术题做错了,他直接用竹条子打到她脸上,当时皮肤就紫了。”
第一次离婚诉讼在2022年10月立案,一个月后开庭,陈若莲提交了男方与其他女性言语暧昧的聊天记录、她给男方的转账记录、家暴伤情鉴定等材料。同时,她向法院申请了人身安全保护令。法院为陈若莲发出了县城首封人身安全保护令,同时驳回了她的离婚诉求。
陈若莲觉得自己的经历没有在庭审中得到同情,“法官没有给我说话的机会,每当我想说话,他就打断我,在讲到伤情鉴定时,男方说掰掉的是甲片,我说不是,法官让记录员过来看我的手,看掰断的指甲是真的还是甲片。”
在等待第二次起诉期间,她时常遭受男方的电话骚扰,“时时刻刻都有电话或视频打进来,我只能关机。我联系他的时候他又不接。”因为要实施分居,陈若莲无法回家探望女儿,每天睡前都忧心女儿会不会遭受家暴,“我女儿也想快一点跟我出来,有一次她跟我说,一分钟也不想待在家里。”
2023年9月陈若莲第二次提起离婚诉讼后,男方的准备充足了许多。他首先向法院提起了管辖权异议,辩称自己的户口和常住地都不在H县城,唐一菲不得不补充男方在H县城生活的证明。在拖延的两三个月的时间里,男方等待定期存款到期,取出了21万元现金,在后来的庭审上,他说这笔钱因赌博输掉了。据唐一菲回忆,法官虽然质疑男方提出管辖权异议的动机,却没有足够证据认定他转移财产。
在第二次诉讼过后,陈若莲拿到了她想要的离婚判决和女儿的抚养权,得到了两套房产中还欠有贷款的那一套,“我现在离婚等于一无所有,还分到了所有的债务。”
被遮蔽的“家暴”
旁听过数十场庭审的贺欣用“职业”来形容他遇到的法官们,“他们不是从共情的角度来思考,如果情绪完全跟着当事人走,他们做不了工作。”
贺欣对广东的一件离婚案印象深刻。原告是一名40岁的女性,当法官问她为什么要离婚时,她说丈夫对她实施了六百多次家暴,不仅打她,还打他们的孩子。这名女性在庭上的讲述情绪激动、细节丰富,使得贺欣马上相信了她的话,但贺欣知道,这是“外行的想法”,法庭需要的是证据,法官冷静地提问,是否有拍摄到家暴的监控录像。
根据司法大数据离婚纠纷专题报告,在全国离婚纠纷一审审结案件中,女性原告占比高达70%以上。论文《诉讼话语视角下的女性诉讼离婚难研究》指出,女性在诉讼中通常使用非直达要点的、情境化的、解释性的关系型表述方式,而法官更偏好直接的、高效的男性化的规则型话语。意味着女性当事人内心的控诉不仅难以引起共情,有时还会让女性处于劣势状态。
论文以湖南省益阳市南县人民法院的庭审记录为材料,其中摘录的一段庭审记录显示,女方的发言频频被法官打断,而男方则会直接、肯定地回答法官提问,并且给出更加具体的时间、数字等等。
在贺欣记录的那场庭审中,女方控诉完男方家暴后,法官立刻问男方是如何打“女方”的,男方的讲述平淡得多,但或许是不熟悉法律,他在言语间承认了有过掐脖子的举动。法官后来告诉贺欣,这份证词已经足够认定家暴,不需要再收集监控录像。然而,在接下来的调解阶段,法官没有再提起家暴这件事情,分财产也是公平分配。
贺欣通过研究得出结论,法院很少认定家暴,因而很少给予受害者经济赔偿。在主动撤诉、调解和好、不准予离婚等情况下,讨论家暴不利于维持婚姻形式;在调解离婚时,为了使得双方达成一致,法官会保持相对和谐的氛围,讨论家暴会招致施暴者的抗拒;而在判决离婚中,为了让双方都能接受判决结果,做到真正的“案结事了”,法官也会沿用调解的思维。
“原本子女抚养权、婚内财产等要素是分开的事情,都有清晰独立的法律规定,为了维护当事人的权利,首先是按照法律的规定来划分,在有家暴的情况下,要对家暴受害者做一些补偿。”贺欣解释,但在实际判决中,为了安抚不愿离婚、心怀不满的一方,“想离婚的当事人,都要做一些财产和抚养权上面的让步。”
“你要不要争”
“我希望抚养两个女儿。”两次提起离婚诉讼,杜雯的诉求都没有改变。
杜雯一直记得小女儿出生时丈夫嫌弃的眼神,他话说得毫不客气,“又是女儿,我都没有脸出门了。”大女儿出生时,丈夫就不高兴,向她质问,为什么医院产房里十有八九是男孩,她却生了个女孩。
2018年,小女儿10个月大时,突发癫痫,后来被诊断出患有自闭症,杜雯的丈夫依然不管不问。杜雯一家以前住在村里,离镇上远,每次带孩子去镇上看病,都得麻烦村里的邻居。有时候杜雯想让丈夫和婆婆帮忙带孩子,他们会反问,“谁让你生的?”
在丈夫家里,杜雯几乎没有感受到尊重,“女儿生病的时候,他跟一起做生意的女人搞暧昧。有一次喝醉酒后,他说让我别管他,带我的小孩就行,随便他怎么搞。”丈夫在镇上做猪肉生意,杜雯也会去摊位上帮忙,但她的劳动没被尊重,“他总是说,钱是他一个人挣的。”
吼骂声总是突然来临,在照看摊位时,杜雯没按照丈夫说的去做,会当众被骂。他们去县城选房看装修时,丈夫要订黑色的室内推拉门,杜雯说了一句“想要白色的”,丈夫立即在店内大发脾气。杜雯和丈夫吵架时经常提到“离婚”,但她觉得自己思想保守,承受不了村里人的眼光,父母也不希望她离婚,所以一直忍着。
大女儿上小学后,杜雯带着两个女儿在县城租房住,与丈夫的矛盾进一步加深。丈夫每个月给杜雯2000元生活费,其中包括日常生活开支、教育费用、租房费等等,“不会多给钱,也从来不会干脆地给。”每月的生活费总是不够用,在小女儿病情好转、大女儿也能帮衬照顾妹妹后,杜雯不得不在县城里找了一份工作。但据她了解,猪肉摊一年的收入有三四十万元,钱全掌握在丈夫的手中。
2022年,杜雯最终下定决心离婚,因为丈夫一直逼她生三胎,“他说不生儿子不甘心”,但她想起之前独自坐月子、照顾孩子的经历,不想再生育了。从决定诉讼离婚开始,杜雯就没想过和好的可能,“已经吵吵闹闹这么多次了,如果闹上法庭后再回去,他更加不会把你当回事。”也是从正式沟通离婚开始,丈夫几乎不再支付孩子的生活费。后来梳理证据时,唐一菲统计到,两年间丈夫转给杜雯的钱只有几千元。
第一次离婚诉讼判不离,杜雯有心理准备。2023年底第二次起诉离婚,双方最大的争议点在于孩子的抚养权。大女儿年满8岁,表示想跟杜雯一起生活,小女儿从出生后一直由杜雯和姐姐照顾,她们一起生活更有利于孩子成长。但在庭审中,男方坚持要求至少一个孩子的抚养权,并且要求孩子实际跟他一起生活。
男方认为将抚养权和一半的房产交出去,是在“花钱养别人的小孩”。而杜雯不相信男方有照顾孩子的耐心,尤其小女儿患有自闭症,“她比同龄的孩子要‘笨’一些,生活自理能力差,吃饭要吃很久。”
双方僵持不下,庭审没有当众宣布结果,之后杜雯向法官询问判决结果,法官问她,“房子你要不要分?”杜雯说,“肯定要分,这是夫妻共同财产。”法官再问,“小孩抚养权你要不要争?”杜雯说,“抚养权要按照法律来判。”
唐一菲发现,杜雯的身上有一种母性的坚韧。很多女性因为急于离婚,会轻易地放弃自己的合法权益,在与杜雯的离婚案时间相近的另一个案子中,原告在调解时激动地跟法官说,“只要能离婚,我什么都不要。”杜雯的经济实力处于弱势,她想为孩子争取更好的物质条件,原本大女儿喜欢舞蹈,她给报了兴趣班,在丈夫不出生活费以后,女儿突然说不想学了。
杜雯难以查清以往的家庭收入,也不知道丈夫有多少存款。在当地的司法实践中,只有以具体的银行名向法院提出申请,甚至提供银行卡号,法院才能为当事人查配偶的银行流水。杜雯申请查询了两所银行,但没有发现对方的存款。在这样的情况下,房子的一半所有权和抚养费是杜雯能争取的最后保障。其实杜雯心里没有着落,只能寄希望于法律,“按照我对他(男方)的了解,是不会给抚养费,但是法院肯定有妥善的处理方案。”
第二次离婚诉讼也被驳回了,杜雯很失望,“我不知道法院为什么不判离,我要继续第三次诉讼了,拖着对谁都不好。”
制度的末端
法院并非独立于真空之中,贺欣提出过一个概念“embedded course”(嵌入的法院),“法院是镶嵌在社会里面的,自然或不自然地受到法外因素的制约,例如制度和行政管理上的影响。”
不断上升的案件数量使得法官追求更有效率的办案方式,确保不引发当事人的极端反应则使法官需要更为平衡地作出决定。这两项不仅仅是现实的办案压力,而且是考评法官的指标,结案数和法定审限内结案率对应为“效率”,而案件被改判发回重审率、一审服判息诉率、信访投诉率等则是要求“维稳”。
现实情况和行政制度都要求法官更高效、更安全地处理案件,反映在离婚案中,就形成了“首诉不离”、“拖延判决”等做法。用贺欣的话来说,“在离婚案中,一方要离、另一方抗拒离婚的情况下,非常容易出事情,出于效率和维稳的考虑,很难完全按照法律来判。”
法院对于离婚案的判决方式,又影响了婚姻家事律师的工作方式,有的律师不接第一次诉讼离婚的案子,有的律师会劝说当事人协议离婚。四川成都的谢女士从怀孕期间开始遭到丈夫贺某阳的严重家暴,她提出离婚,被拒绝,律师以“起诉离婚耗时长”为由,建议她继续协商离婚。
随后两年,谢女士依然没能离婚,并在2023年4月的家暴中被打成重伤,多处器官受伤,需终身挂粪袋。直至2024年5月31日,谢女士的离婚案开庭,法院判决准予离婚。
“婚姻家事的案子越来越麻烦。”这是唐一菲的从业感受,她在7年前开始涉及离婚案,2018年底选择将婚姻家事案作为主要的职业方向,“《民法典》出台以前,离婚案很好做,当事人可以在第一次起诉时获准离婚,我们不用费力调解。但现在我们要费尽心思跟对方谈判,即使己方当事人是无过错方,但为了协商一致,要去满足对方的条件,不然当事人就要被离婚程序拖累,也很难通过判决达成离婚。”
唐一菲目前任职的律所是湖南省唯一一家专做婚姻家事案的律所,与其他律所在收费方式上有明显的不同,委托人一次性付费,律所提供全程服务,直至离婚,以此来提高律师的调解率,让律师和当事人在时间效益上达成一致——越早离婚,收益越大。在律所精选的案例集中,不难看出效率的导向性,案例名称诸如“巧妙启动诉讼表达离婚决心,帮助当事人快速调解离婚”、“双方拉扯无数个日夜,律师巧妙调解促成协议离婚”。
如果调解不成进入诉讼程序,当事人也不用担心因诉讼失败而被律师拒绝,事实上,诉讼离婚的程序阻止不了下定决心离婚的人。据唐一菲估算,“能走到请律师去起诉这一步的人,90%都会进入第二次起诉的。”
尽管基层法院在实际案件审理中遇到现实困难,但在制度层面,地方和最高人民法院在不断完善条例和法律,更加注重对婚姻中经济弱势一方的保护。
2024年3月27日,福建省人大常委会会议表决通过《福建省妇女权益保障条例》,其中第四十五条规定,“妇女持身份证、户口本和结婚证等证明夫妻关系的有效证件,可以依法向房地产行政管理、车辆管理等单位申请查询配偶的财产状况,有关单位应当受理,并且为其出具相应的书面材料。”这一条例针对地域内大多数家庭由男性控制财产的实际情况,进一步保障了妇女在婚姻中的财产知情权。
对于离婚经济补偿,《民法典》第一千零八十八条已有规定,“夫妻一方因抚育子女、照料老年人、协助另一方工作等负担较多义务的,离婚时有权向另一方请求补偿,另一方应当给予补偿。”但如何补偿没有明确说明,在诉讼实践中也很少被提出。
而在2024年4月7日最高人民法院发布的《民法典婚姻家庭编的解释(二)(征求意见稿)》中,补充了详细的认定和处理方法,“人民法院应当根据婚姻关系存续时间、负担相应义务投入的精力及对双方的影响、对家庭所做贡献程度、双方离婚时经济状况以及给付方负担能力、当地收入水平等事实,确定补偿数额。”
全国妇联权益部答记者问时表示,离婚经济补偿制度是“对家务劳动价值的认可”,“人的时间和精力是有限的,一方承担了较多家务劳动,必然会影响提升自身职业能力以及其他能力的时间和精力,作为受益的另一方,于情于理,给予对方一定补偿理所应当。”
贺欣对司法解释的征求意见稿持积极态度,“它是保护女性的。”通过大量研究和观察,他发现女性在离婚诉讼过程中是明显的弱者,“整个社会的两性不平等问题,会反映到离婚这个节骨点上。”普遍性的状况仅凭个别法官的性别意识觉醒无法改变,唯有立法和制度的改善才能导向一个更和谐平等的社会。
诉讼离婚困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