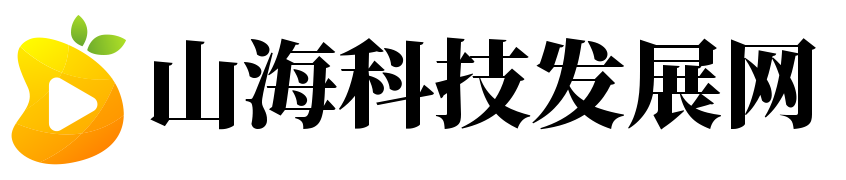中世纪的人们每晚睡两次觉

研究发现,中世纪的人们每晚都是双阶段睡眠,他们不是一觉到天亮,而是分两次睡:大家会在午夜过后的某个时刻醒来,该工作的工作,该祈祷的祈祷,该偷窃的偷窃,该造人的造人……然后再回到床上睡觉休息直到天亮。
在中世纪,大多数人都会在日落时分上床,两个阶段的睡眠时间大致相同,为4-5小时。
当然,不是每个人都按照同样的时间表睡觉。越晚睡觉的人,在最初的睡眠后就越晚醒来;或者,如果他们在午夜后就寝,他们可能直到黎明才醒来。因此,在《坎特伯雷故事集》的《乡绅的故事》中,卡娜西在“夜幕降临后不久”就睡了,随后在“第一次睡眠”后的清晨醒来;反过来,她的同伴们熬得更晚,“一直睡到天亮”。
夜间醒来的时间通常从23点左右持续到1点左右,这取决于他们上床的时间。它往往不是由夜间的噪音或其他干扰引起的——也不是由任何种类的闹钟引起的。相反,醒来完全是自然发生的,就像在早晨一样。
夜晚的第一次睡眠叫“初睡”(first sleep),它在整个前工业化世界被广泛采用。在法国叫“premier somme”,在意大利叫“primo sonno”。事实上,在遥远的非洲、南亚和东南亚、澳大利亚、南美和中东等地都发现了这种习惯的证据。
随后的清醒期被称为“守夜”(the watch)——它是一个相当有用的时机,可以完成一些事情。在月亮、星星和油灯或“灯心草灯”的微弱光芒下,人们会处理一些普通的工作,如往火里添柴、吃药或去小便。
对于农民来说,起床意味着重新开始更严肃的工作——无论这涉及到提心吊胆地出去检查农场动物还是从事家务劳动,如修补布匹、梳理羊毛或剥去要烧的灯心草。
自然,犯罪分子也趁机鬼鬼祟祟,制造麻烦。例如约克郡东区的卢克·阿特金森。一天晚上,他设法在清晨的睡眠中挤出时间进行谋杀——而且据他的妻子说,他经常利用这段时间到别人家去干坏事。
但最重要的是,守夜对社交是很有帮助的。当时,大多数人都是睡在一起的,他们经常发现自己与各种臭虫、跳蚤、虱子、家庭成员、朋友、仆人以及——如果他们在旅行——还有完全陌生的人亲密地依偎在一起。
为了最大限度地减少尴尬,睡眠涉及一些严格的社会惯例,如避免身体接触或过多的躁动,并且有指定的睡眠位置。例如,女童通常会躺在床的一侧,年龄最大的离墙最近,其次是母亲和父亲,然后是男童——同样按年龄排列——然后是非家庭成员。
人们经常会呆在床上聊天。在那些奇怪的黄昏时间里,同床的人们可以分享一种非正式的、随意的谈话,而这在白天是很难实现的。
对于那些与他人同床共枕的人来说,这也是一个方便亲热的时间间隔——如果他们经历了一天漫长的体力劳动,第一次睡眠可以缓解他们的疲惫,之后的一段时间是造人的绝佳时机。
在这段清醒时间里,中世纪圣本笃会的僧侣们足以在通常的凌晨2点和3点之间的晨祷中做祈祷。
一旦人们清醒了几个小时,他们通常就会回到床上去。接下来的步骤是“晨睡”(morning sleep),可能会持续到黎明,或更晚。就像今天一样,人们最终何时醒来,取决于他们上床的时间。
那么,两次睡眠为什么后来又消失了?
总的来说,这项研究或许提供了一个解释,即为什么从19世纪初开始,大部分人类放弃了两阶段睡眠系统。就像最近我们行为上的其他转变一样,例如转向依赖时钟时间,答案是工业革命。
1667年,巴黎成为世界上第一个照亮街道的城市,在玻璃灯中使用蜡制蜡烛。同年,里尔紧随其后,两年后,阿姆斯特丹也开发出了效率更高的油灯。
人工照明变得更加普遍,而且更加强大——首先是煤气照明,这是伦敦有史以来第一次引进的,然后,当然是在19世纪末的电灯。除了改变人们的昼夜节律外,人工照明还自然而然地使人们能够更晚睡觉。评论配图
除了改变人口的昼夜节律外,人工照明还延长了第一次睡眠时间,缩短了第二次睡眠时间。为了工作的需要,很多人开始早起,半夜醒来和第二次睡眠变成了只是在床上翻身,多打了10分钟的瞌睡而已。
最初的转变可能是由于街道照明的改善、家庭照明和咖啡馆的激增——这些咖啡馆有时整夜营业。随着夜晚成为合法活动的场所,并且随着这种活动的增加,人们可以用来休息的时间长度也在减少。
美好的上半夜成为了一种时尚,花几个小时躺在床上是浪费时间的。经济组织的变化变得更有效率,使工作常规化,让大量的人在同一时间出现在工厂车间,以尽可能集中的方式做尽可能多的工作。睡眠时间因此受到挤压和合并。
第一次和第二次睡眠的说法在17世纪末开始消失。这开始于北欧的城市上层阶级,并在接下来的200年里渗透到了西方社会的其他地方。
即使人工照明不完全是罪魁祸首,到20世纪末,两次睡眠之间的划分已经完全消失了——工业革命不仅改变了我们的技术,也改变了我们的生物特征。